2011年5月27日 星期五
[讀劇] 《又是同志戲》
『我以為悲劇最重要的一幕是第六幕:』(辛波絲卡)
微微興奮地讀完《又是同志戲》劇本了,艷異之餘,心底百感交集,我本來以為會看到歌舞青春,年華無敵奔竄的,恕我有如此不切實際的想像......我在想,名為《又是同志戲》,如此引人側目;但在我讀這齣戲時,在給定的『現實』第二層,我完全都笑不出來(是吧,這是悲劇吧,結局驚悚,卻又意欲升揚,真是荒謬至令我錯愕),那種感覺大概就跟讀報同志社會新聞一般,雖是『戲中戲』,從社會批判的角度來看,我看到的確實是『戲』,裡面每個刻板角色,操演錯位之間,令人眼花撩亂,似乎有帶有一點關於跟『同志經驗』相關,可以繼續發揮、伸延的......這裡頭二元對立過於森嚴,雖說可能趕時應事了『小三』、『忠與不忠』等鹹魚芒果話題,但這些子題及人性、關係,卻仍有待商榷,當然,這齣戲的缺點,或者便是其所心心念念所要批判、解套的形象、氣質本身,人從他者所映照的鏡象與己身之間的衝突,他者真是是他者那樣,而己身又何以不可以是自己這樣,自在、開心而已,結局絕對不是絕局,在恐同或嘩眾的取捨之間,似乎要第三層結構才解,《又是同志戲》絕對不能只是通俗劇那樣的『道德審判』而已,作為婚姻關係裡的異性戀導演的遮掩及情慾,難道真的不如珍妮和編劇的情操令人同情或力行嗎?
性別、性行為、形象的固定或流動別過不談。那撐起整齣戲的『珍妮』之英雄化、犧牲付出式的人格反倒顯得矯飾了,其內心交戰或可加大力度,救贖,或跟青青之間戲中戲互動或許可以再拉出肉慾一段,再接到我頗為喜歡的巴掌那段)父權或說男性異性戀霸權作為想像中所欲戳破的紙老虎,其風流可惡之處,不正是其可憐之處?而編劇只能落入傳統孩子正朔之爭奪復仇戰嗎?這樣要以小搏大的干涉力道,要引人更進一步深思去標籤、或去汙名似乎有其侷限之處。
戲中所見,權力慾望投射在編劇身上,也妒忌,也審判,也救贖,也主導(詮釋)了戲中戲的走向,女編劇反倒成為霸權的支配及代言人了(繼承權不正是萬世一系的史觀嗎),又妖魔化、又神格化(一無所知作為理解的起點,氣節與森嚴不可侵的肉體才是王道?就算怎樣也都是被逼上刀山魚水之鍋的),這究竟是誰的場子,女性真的翻身了嗎?而負責聲色犬馬打燈暗燈的凱迪,難道真無法照亮他己身的困境,或者獨角顯現其初始的滿懷期待或情欲的反覆煎熬(流言,就更不貼近可能的任一真實嗎),只能覆著沒有交代或任何打算的的標籤之孤單角色、恐怖分子般,走進所欲批判的殺夫式的奇觀社會新聞之結局,這是血淋淋自陷的社會批判,或僅僅是一個『異難忘』男同志肉體無法得寵,索愛不著(或流言、或利用)、由愛生恨,花果飄零的『內心荒謬風景』(反映著矛盾掙扎的邊緣心態)呢?這樣,似乎得不到觀者深究,投以更熱切的注視與心有戚戚焉的註解,凱迪的處境可能還得更完善;至此,我想起近幾年我觀察到的同志運動的一些現象......王子復仇驚悚剪臍的剪刀、由不同人嘴中聲聲的控訴、楚楚可憐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風中殘燭們吶,故事的不斷轉述,似乎也有疲乏之餘......
劇末拉子珍妮對「化療中(電椅/治療/苦難=激爽)」的安娜說:『安娜,妳看,我剪了和妳一樣的短頭髮耶』身份乃至認同作為絕症患者,盡皆斬斷髮絲(這大時代大敘事之於我們樣態世態不由己身的力線懸絲、綁縛、服飾符碼乃至肉身特徵形貌的略欲)這一隱喻,難道真只能被他者剪出他者想像中的樣子嗎?或者影子與薄影被剪,虹與霓互剪,甚至帶淚可喜的自梳妝點,這林林種種光繁葉綠得一切,當然不止於標題,而是意味深長的備忘錄又一章......
訂閱:
張貼留言 (Atom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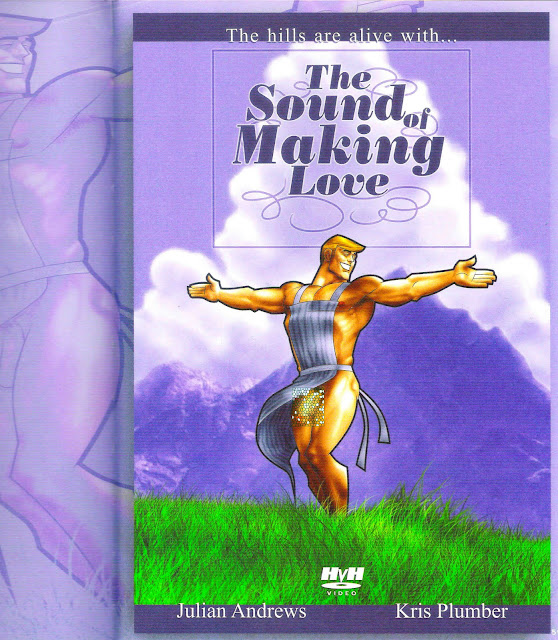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